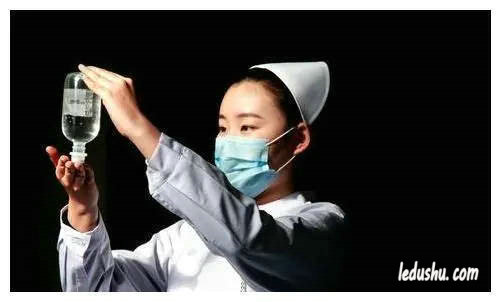“抬鼓儿抬,尼龙袜子,当当鞋(hai)……”儿时的歌谣似乎还在耳畔回荡,转眼已是不惑之年。
为了潮流与时尚,虽多年不穿布鞋了,但脚知道,那双母亲亲手做的布鞋,穿上是多么的舒服。
小时候做梦都想穿上一双走路能发出“当当”响声的鞋,是多么美气、洋气啊,布鞋就是踢踏烂都不会走出这样的动静来。
别人说起我母亲时,都说她有一双巧手,做的布鞋就捋吃(好看)着,装脚着,好地了不得。经常有邻居找母亲剪鞋样子,每次别人说母亲布鞋做得好时,她的脸上就堆起如同开花一般的笑容,好比别人夸她养的娃娃个个都心疼一样。在我的记忆里,母亲一直是忙碌着的,即就是下雨下雪天,手都不闲着,不是拧麻绳就是糊锲子,不是纳鞋底就是缝鞋口,做好的新鞋压在箱子里,隔上些日子,和数鸡蛋一样,把布鞋一五一十地数上一遍,然后阔阔(轻轻)地盖上箱盖,捋上一把头发,很有成就感地长长舒口气。
这样的画面,已经永久定格在了我的脑海里。
“多好看的新鞋有一夹,多贤惠的阿家(指婆婆)有一发。”这是我们穿新鞋时,母亲总挂在嘴上的话。
的确,穿新布鞋,脚是要受几天罪的。
如果新鞋一下子就能蹬进去,过不了几日,鞋肯定就走样了,松垮了,甚至在玩耍跑步的时候,飞出去也是有可能的。所以,能穿上一双捋吃(好看)的布鞋,勾鞋时把手指头夹里面是常有的事,疼得“嗷嗷”直叫。清晨伴随堂屋摆钟节奏声的,还有穿新布鞋,踢在门墩上,炕沿上,还有门口的踩石上“咣咣”的声音。后来父亲想出来了一种办法,就是拿尖嘴钳子夹住鞋后跟,往上勾鞋,这样就不夹指头了。穿上新布鞋,真是要使出吃奶的力气,不知道嘴里要发多少牢骚,嫌弃母亲多少回。小时候调皮,一双布鞋在我脚上踢踏不了几日,大拇指头就雄赳赳气昂昂地露出来了。那年月大家都无所谓穿破鞋,谁也不会笑话谁,因为都穿破鞋。母亲看见我的鞋破了,嘴里嘀咕:“拐子上哪来那么多的劲,像是长了牙齿一样,啃着呢,还是嚼着呢,脱下来,我给你补补!”“补的鞋我才不穿呢,你以为你做的鞋好得很!你在点花(显摆)我让我爸给我买一双“当当”鞋恰,把你做哈的务尔(扔)出去都没人拾!”话还没说完,赶紧撒腿跑,不然少不了一顿笤帚疙瘩。母亲给我做布鞋时,鞋面总是要多加几层布,鞋尖还要多加一层跳绒(做鞋最长用的一种不料),这样鞋面破了,下面还有一层和鞋面一样的布,免得再补。其实,鞋面越厚越结实,做出来的布鞋越没样子,太厚了做不出那个巧,能上到鞋底子上就已经不错了。那时候最不爱穿的鞋就是布鞋,心想,都说母亲手巧,我不知道巧在哪里,但母亲给姐姐、哥哥做的鞋都特别娇(合适),那时我怀疑母亲是故意的,所以穿上布鞋也就死里没命地跌拌(玩耍),看布鞋能早点开线、早点破不——当母亲做的新布鞋接不上茬的时候,父亲就会给我买“当当”鞋。可是,越是这样,母亲给我做的布鞋就越结实,所以,经常为穿新布鞋夹脚和母亲争吵,也经常把自己被气哭。随着年龄的增长也没那么调皮了,布鞋也就没那么费了,母亲给我做的鞋也越来越娇了。黄土地上的女人对家人的爱都离不开那双巧手,或是汉子肩上缝的一块补丁,或是家里枕头顶上绣的鸳鸯,而更多是给家人做一双双布鞋,没有轰轰烈烈地爱,只有细水长流的日子。
穿上布鞋丈量岁月的日子一去不复返,发现自己已经好久好久没有穿过布鞋了。一年四季都穿着小时候梦寐以求的“当当”鞋时,却走不出儿时的快乐。
前些年,母亲还一如既往地给我每年做一双新布鞋,等我回家过年了穿,白毛底子黑条绒的,针脚非常细密,那鞋真叫一个捋吃!母亲害怕新鞋夹我的脚,就让父亲给我先踏壤上几天,等我回家过年穿时不再夹脚。
带着疲惫穿着皮鞋回家过年,一声“妈哎!我回来了”,让人无比的幸福。母亲一边答应边打起门帘,让我赶紧进屋,嘴里一直说:“额的娃来了,年就欢了。”父亲则一旁提醒母亲:“赶紧把你做的新鞋拿来让娃换上,把脚缓卡。你不是把你做的鞋天天三摸两揣的,想娃了就揣鞋哩,这不是娃来了,你却愣住了。”“哦哦哦,你看我这记性!”说着,母亲便转过身去,从箱子里取出布鞋,边拍打,边用嘴“噗噗”地吹:“赶紧穿上,你爸给你壤开着哩,不夹脚,你穿上我相端相端(仔细打量)。”母亲边看边揩去眼角的泪花,自言自语道:“能成,能成,好得很!”脱下皮鞋,脱掉了束缚,穿上布鞋,一身轻松,好像又回到了小时候。后来母亲知道我们穿布鞋的日子少,索性不做了。她眼睛不好,我们也不让做,她倒给自己和父亲攒下了一箱子布鞋,谁知父亲没穿几双就撇我们而去,留下了的那些新布鞋,成了母亲永远的念想,想父亲了,就把布鞋再一五一十地数上一遍,然后阔阔地盖上箱盖,就这么静静地想着。近年母亲虽然一直随我在城里生活,但还惦记着她的一箱布鞋,再三叮嘱大哥,过些日子了晒晒,别朽在箱子里。千里之行,始于足下。现在想来,母亲做的布鞋虽然走不出响声,可穿上它,踏实。(本文系作者原创,欢迎转载或选用)
作者简介

蔡金喜,笔名蔡全、童安,甘肃秦安人,现居兰州。爱好文学,寻求心灵纯净,向往诗意安静的生活,闲暇时信笔涂鸦,自娱自乐。